莫言終于出新作了——一下子在第9期《人民文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了劇本《錦衣》,,加七首詩(shī),。這至少讓讀者的好奇心和期待感在數(shù)年之后,稍稍滿足了一下,,讓那個(gè)“諾獎(jiǎng)魔咒”的魅影暫時(shí)退到了遠(yuǎn)處,。

莫言
還是那個(gè)莫言,那個(gè)一向奇幻而詼諧,、接通著鄉(xiāng)土民間的莫言,,那個(gè)滿帶著煙火氣息、牽連著高密東北鄉(xiāng)根根須須枝枝蔓蔓的莫言,,那個(gè)來(lái)自地方性的原汁原味與五花八門(mén)的,、一向有著蓬勃感性和豐沛戲劇感的莫言。從小處說(shuō),,他以此再次印證和強(qiáng)調(diào)了他自己的寫(xiě)作風(fēng)格,,證明了他作為一個(gè)作家的戲劇能力,強(qiáng)調(diào)了他鮮明強(qiáng)烈的戲劇性追求與詼諧感的詩(shī)意,;從大處說(shuō),,他是用四兩撥千斤的方式,不經(jīng)意而又實(shí)實(shí)在在地延續(xù)了純文學(xué)意義上的當(dāng)代戲劇——這種古老藝術(shù)的氣脈,。從他的《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蛙》,到這部《錦衣》,,他的戲劇創(chuàng)作頗有可觀之處,,更兼他幾乎用了“戲劇體”寫(xiě)成的《檀香刑》,還有更多具有濃烈戲劇性的長(zhǎng)篇,,莫言構(gòu)成了在文體與形式,、語(yǔ)言和美學(xué)上的另一個(gè)現(xiàn)象。他再次用不凡的創(chuàng)造力證明,,純文學(xué)意義上的戲劇乃至戲曲并沒(méi)有遠(yuǎn)逝,,關(guān)漢卿、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的氣脈仍然活在我們的當(dāng)代,。 莫言應(yīng)邀題寫(xiě)的篇名
莫言應(yīng)邀題寫(xiě)的篇名
似乎話說(shuō)得有點(diǎn)大了,。我的意思是,依然可以靠著杰出作家的創(chuàng)造力,,來(lái)延續(xù)文學(xué)的核心要義,,包括戲劇與戲曲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生命力,包括小說(shuō)本身的戲劇稟賦,,敘事的戲劇性與詩(shī)意等等,。這些問(wèn)題事關(guān)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復(fù)雜的本體論問(wèn)題,,需要擇機(jī)細(xì)加討論,。但有一點(diǎn)可以肯定,,莫言在當(dāng)代作家中,在文體方面是最“無(wú)邊界”的一位,,他對(duì)藝術(shù)形式的混合雜糅與創(chuàng)生再造的能力,,實(shí)在是令人瞠目。
《錦衣》敘述了一個(gè)似曾相識(shí)的故事:清末之際,,正值民不聊生,,百業(yè)凋敝,污吏橫行,,妖孽四起,,留日的愛(ài)國(guó)青年秦興邦和季星官喬裝夫妻潛回鄉(xiāng)里,圖謀舉事,。路見(jiàn)大煙鬼宋老三沿街賣(mài)女宋春蓮,,季星官一則感慨不平,二則一見(jiàn)鐘情,。但很快,,二人被捕快爪牙識(shí)破,,秦興邦逃走,,季星官詐死潛藏,。中間穿插了順發(fā)鹽鋪掌柜,,季星官的寡母,,媒婆王氏及其官府鷹犬的侄子王豹,,還有賣(mài)官鬻爵,、魚(yú)肉鄉(xiāng)里的高密縣令莊有理和莊雄才父子的重重糾葛,。王婆,、王豹因圖謀鹽鋪錢(qián)財(cái),,設(shè)計(jì)讓季母為遠(yuǎn)在東洋留學(xué)的兒子先行娶妻,致使季母讓兒媳春蓮與一只公雞成親,。而王豹與莊雄才均垂涎春蓮美色,,數(shù)度前來(lái)糾纏,春蓮誓死抗?fàn)?,危急時(shí)刻季星官潛回家中為春蓮療傷,,兩情繾綣,終成夫妻,。不料為偷聽(tīng)者王婆告發(fā),,莊氏父子帶兵前來(lái)捉拿,正好被秦興邦和季星官所發(fā)動(dòng)的義軍擊敗,,王豹等爪牙則乘勢(shì)投機(jī)反水,,捉住莊氏父子。 劇情的混合意味非常明顯,,也像是《阿Q正傳》或者《茶館》,,甚至莫言自己的《檀香刑》中的某些場(chǎng)景:有革命和近代史,,更有民間生活場(chǎng)景、傳統(tǒng)戲曲原型等,,互相雜糅,,成為一個(gè)離奇曲折、跌宕起伏的故事,。以作者自述的話說(shuō),,“故事原型”為“革命黨舉義攻打縣城的歷史傳奇與公雞變?nèi)说墓砉止适氯诤显谝黄穑蔀橐嗾嬉嗷弥牢谋尽?。這里有英雄救美,,有移花接木,有善惡必報(bào),,也有偷梁換柱,,種種舊戲中常見(jiàn)的結(jié)構(gòu)與主題,在其中都有體現(xiàn),。當(dāng)然,,最重要的是,它再度深入探究和處理了近代中國(guó)的革命與社會(huì)問(wèn)題,,既生動(dòng)再現(xiàn)了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各種弊病,,披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又從文化,、制度,、倫理甚至文明的層面,深入揭示了歷史,、社會(huì)變革的深層次原因??梢哉f(shuō),,莫言以他獨(dú)有的戲劇性筆觸,通過(guò)人物的對(duì)話,,活脫脫將其彰顯無(wú)遺,。
劇情的混合意味非常明顯,,也像是《阿Q正傳》或者《茶館》,,甚至莫言自己的《檀香刑》中的某些場(chǎng)景:有革命和近代史,,更有民間生活場(chǎng)景、傳統(tǒng)戲曲原型等,,互相雜糅,,成為一個(gè)離奇曲折、跌宕起伏的故事,。以作者自述的話說(shuō),,“故事原型”為“革命黨舉義攻打縣城的歷史傳奇與公雞變?nèi)说墓砉止适氯诤显谝黄穑蔀橐嗾嬉嗷弥牢谋尽?。這里有英雄救美,,有移花接木,有善惡必報(bào),,也有偷梁換柱,,種種舊戲中常見(jiàn)的結(jié)構(gòu)與主題,在其中都有體現(xiàn),。當(dāng)然,,最重要的是,它再度深入探究和處理了近代中國(guó)的革命與社會(huì)問(wèn)題,,既生動(dòng)再現(xiàn)了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各種弊病,,披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又從文化,、制度,、倫理甚至文明的層面,深入揭示了歷史,、社會(huì)變革的深層次原因??梢哉f(shuō),,莫言以他獨(dú)有的戲劇性筆觸,通過(guò)人物的對(duì)話,,活脫脫將其彰顯無(wú)遺,。 當(dāng)然,民間生活場(chǎng)景依然是重要的,。買(mǎi)賣(mài)婚姻與婆媳關(guān)系,,說(shuō)媒拉纖與混世青皮,近代中國(guó)的衰敗與流氓文化的盛行,,其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在這部劇作中可謂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當(dāng)然,民間生活場(chǎng)景依然是重要的,。買(mǎi)賣(mài)婚姻與婆媳關(guān)系,,說(shuō)媒拉纖與混世青皮,近代中國(guó)的衰敗與流氓文化的盛行,,其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在這部劇作中可謂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在藝術(shù)的譜系上,,《錦衣》的復(fù)雜性更是難于匆促說(shuō)清,。竊以為,,其中有關(guān)漢卿和莎士比亞的影子,有《水滸傳》的胚子,,有魯迅和老舍的骨架子,,更有民間戲曲的各種元素與殼子。感覺(jué)它在奇跡般地復(fù)活地方性戲曲這樣的質(zhì)素與形式,。若是吟詠起來(lái),,完全可以套上不同戲曲的唱念做打,再現(xiàn)一臺(tái)精彩大戲,。按說(shu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現(xiàn)如今沒(méi)有什么人會(huì)對(duì)這般藝術(shù)類型抱有信心,但莫言恰恰就以他點(diǎn)石成金的才能,,彰顯出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生命力,。 還有風(fēng)格。在我看來(lái),,莫言一直在刻意地用“障眼法”或者喜劇性,,來(lái)處理或者中和其作品的批判力與悲劇性。他成功了,。無(wú)論是《酒國(guó)》《檀香刑》還是《四十一炮》《生死疲勞》等,,都是如此?;蛟S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欲揚(yáng)先抑和“錦衣夜行”,,當(dāng)然也是更高意義上的“警世奇幻”,或者藝術(shù)的辯證法,。
還有風(fēng)格。在我看來(lái),,莫言一直在刻意地用“障眼法”或者喜劇性,,來(lái)處理或者中和其作品的批判力與悲劇性。他成功了,。無(wú)論是《酒國(guó)》《檀香刑》還是《四十一炮》《生死疲勞》等,,都是如此?;蛟S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欲揚(yáng)先抑和“錦衣夜行”,,當(dāng)然也是更高意義上的“警世奇幻”,或者藝術(shù)的辯證法,。
莫言有著令人驚訝的感性才華,,在任何情況下,他的觀念都不會(huì)壓倒其藝術(shù)形象,。他的傳神之筆,,寥寥幾下就能夠點(diǎn)活一個(gè)人物,激活一種性格,,展開(kāi)一種話語(yǔ)或腔調(diào),,使之在他的藝術(shù)王國(guó)中披掛上陣,肩負(fù)起譏諷世事,、鞭撻人性的激越使命,。《錦衣》中的人物,,尤其如是,。
(編輯:月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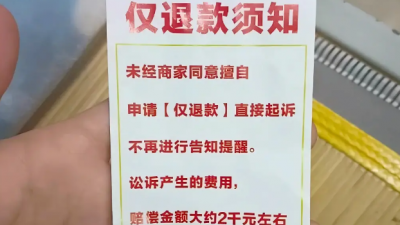

 “護(hù)眼臺(tái)燈”亂象調(diào)查
“護(hù)眼臺(tái)燈”亂象調(diào)查 AI賬號(hào)成起號(hào)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guò)“AI打標(biāo)”背后有哪些隱患?
AI賬號(hào)成起號(hào)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guò)“AI打標(biāo)”背后有哪些隱患? 救命的醫(yī)療設(shè)備,,如何淪為個(gè)人提款機(jī)?
救命的醫(yī)療設(shè)備,,如何淪為個(gè)人提款機(jī)? 原價(jià)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mài)不到百元
原價(jià)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mài)不到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