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現(xiàn)代佛學》期刊發(fā)表一則關于成立大雄麻袋廠的新聞短訊,,新中國首屆政協(xié)會議參加者中唯一的佛教僧侶代表巨贊法師就是大雄麻袋廠的董事長,。他提出,,“麻袋是工農(nóng)必需品,,用途很大。過去依賴印度輸入,。每年的一萬萬條,,約合五千萬美元,占全國進口的第四位,,實在是一大漏厄,。因此中央提倡種麻價值之所在。麻袋,,逐漸達到自給,。據(jù)農(nóng)業(yè)部計劃,,本年增產(chǎn)麻袋二千五百萬條,1953年增產(chǎn)至七千萬條,。所以麻袋業(yè)前途無量,。手工制造,并不十分麻煩,,尤其適合出家僧尼,。”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家僧侶創(chuàng)辦的麻袋廠,,代表著新中國的僧侶開始嘗試“勞動自養(yǎng)”的社會實踐嘗試,。建國初期的中國經(jīng)濟極度衰弱,國民生產(chǎn)領域的價值總額偏低,,物資匱乏,,很多商品要依賴進口,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面臨國際封鎖和打壓,,導致國民生產(chǎn)總值水平較低,。巨贊法師根據(jù)國內(nèi)經(jīng)濟的現(xiàn)狀,結合僧侶的勞動生產(chǎn)能力選擇了手工勞動這種比較初級的勞動環(huán)節(jié),,即可以解決社會需要同時又可以解決僧侶參加勞動生產(chǎn)解決“自養(yǎng)”的問題,。1950年到1952年,在巨贊法師的提倡下京津地區(qū)的佛教僧團先后成立大雄,、大仁,、大力麻袋廠等經(jīng)濟實體,廣大僧侶通過參加生產(chǎn)勞動既解決了自養(yǎng)的問題,,還積極參與了國家建設,,為佛教“生產(chǎn)化”探索了一條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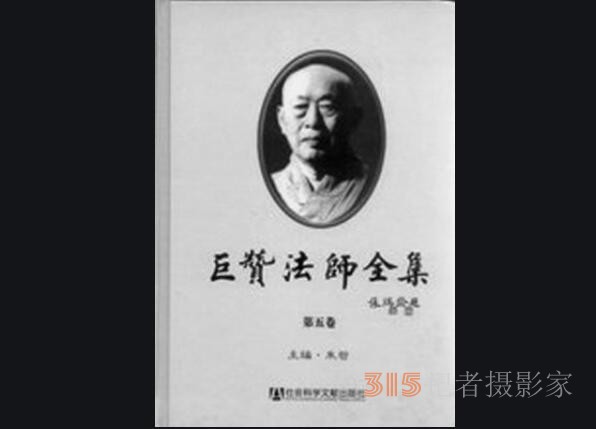
釋巨贊(公元1908—1984年),,江蘇江陰人,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樸,生前任中國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務,。他連續(xù)當選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及第六屆的常務委員,是當代中國佛教界愛國愛教僧侶的典型代表,。他以宗教界人士身份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是唯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的佛教僧侶,。政治上進步愛國,與中國共產(chǎn)黨肝膽相照,,通過創(chuàng)辦工廠等方式,,鼓勵廣大僧侶參加生產(chǎn)勞動,提倡“佛教生產(chǎn)化”,,為佛教積極適應新中國社會進行了有益社會實踐,。
巨贊法師所踐行的“佛教生產(chǎn)化”從形式上看是通過參加社會生產(chǎn)解決僧團的經(jīng)濟問題,從佛教祖制上符合禪宗清規(guī)的傳統(tǒng),,在城市里弘法的僧團沒有土地經(jīng)濟支持,,不能實現(xiàn)“農(nóng)禪并重”的叢林生活,巨贊法師變通了生產(chǎn)形式,,鼓勵廣大僧侶通過參加手動勞動的方式“出坡勞動”,。新中國成立以后,一部分僧侶不愿意參加社會生產(chǎn),,他們比較滿足于依靠居士供養(yǎng)來生活,,由于廣大人民群眾對這種方式比較抵觸,這種“供養(yǎng)”也就慢慢消失了,。不得不參加生產(chǎn)勞動的廣大僧侶對參加手工勞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為此,巨贊法師提出僧侶參加手工勞動的理由,,“我們開辦大雄麻袋廠的目的有三:一是遵照人民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的指示,,使一向過著寄生生活的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產(chǎn),達到自養(yǎng)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產(chǎn)建設,。二是通過學習,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于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神,增進修養(yǎng),。三是以佛教生產(chǎn)事業(yè)維持佛教文化事業(yè)?!睆乃忉屴k廠自養(yǎng)的目的上看,,巨贊法師不僅僅簡單的將“佛教生產(chǎn)化”建立在解決僧團的生存的問題,而是站在清規(guī)祖制的立場,,將辦廠勞動提升到提升佛教信仰的高度,。通過自養(yǎng)獲得經(jīng)濟能力從而弘揚佛法,又通過自養(yǎng)解決生存問題,,在不依靠“供養(yǎng)”的情況下實現(xiàn)“自養(yǎng)”去掉“寄生蟲”形象,。
按照佛教傳統(tǒng)佛教四眾的組織體系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佛教經(jīng)濟分配的閉環(huán),居士供養(yǎng)三寶,,護持佛教發(fā)展,,這就是“護法”,;僧侶精進修行,弘揚佛教,,這就是“弘法”,。“護法”和“弘法”又在佛教衍生體系中實現(xiàn)了佛教事業(yè)發(fā)展的閉環(huán),。佛教經(jīng)濟上的閉環(huán)和佛教事業(yè)發(fā)展上的閉環(huán)成為佛教事業(yè)發(fā)展的兩輪驅動,,促使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系統(tǒng)能夠源源不斷的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文化產(chǎn)品,滿足民眾的精神需求,。這是佛教事業(yè)發(fā)展的“生態(tài)動力”,。
這種“生態(tài)動力”是建立在社會經(jīng)濟基礎豐富的前提下,同時人們又存在一定的精神苦悶,,這種苦悶就是佛教所說的“人生實苦”,,這既是佛教產(chǎn)生的精神基礎又是佛教發(fā)展的精神基礎。佛教發(fā)展的“生態(tài)動力”需要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滿足僧團生存的經(jīng)濟基礎,;二是信教群眾感知“人生實苦”的精神基礎。兩個基礎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從這個“生態(tài)動力”角度理解,只有兩個基礎同時存在而且社會需求旺盛才能保證佛教快速發(fā)展,,雙方形成“供需兩旺”的生態(tài)氛圍,。五臺山碧山寺山門兩側有“護國佑民,法輪常轉”八個字可以完美詮釋“生態(tài)動力”的內(nèi)涵,,這兩句話體現(xiàn)了佛教發(fā)展的兩個基礎,,“護國佑民”就是要求佛教要發(fā)揮積極作用,為社會尤其是廣大信教群眾提供優(yōu)質(zhì)的佛教文化產(chǎn)品,;“法輪常轉”體現(xiàn)對應“護國佑民”的辯證關系,,如果佛教實現(xiàn)不了“護國佑民”的社會作用,那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就會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發(fā)展,?!吧鷳B(tài)動力”是依據(jù)佛教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和教理教義總結出來的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在常態(tài)下這種“生態(tài)動力”是可以實現(xiàn)自驅運轉的,。但是,在社會發(fā)生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一旦這個生態(tài)被打破,,那佛教的發(fā)展就會失去動力。
巨贊法師提出“佛教生產(chǎn)化”就是要僧團實現(xiàn)自養(yǎng),,促使僧團在經(jīng)濟上實現(xiàn)“自主”乃至通向“自由”,,從而確保僧團能夠正常為社會提供佛教文化產(chǎn)品,。巨贊法師解釋創(chuàng)辦麻袋工廠的三個目的可以總結為六個字“自養(yǎng)、修養(yǎng),、弘揚”,,自養(yǎng)就是解決生產(chǎn)問題,巨贊法師解放前就大聲疾僧團要自養(yǎng),,要自力更生,,再靠信眾的“供養(yǎng)”佛教就會走向滅亡。巨贊法師這里所說的“供養(yǎng)”是和“弘揚”相對應的,,如果僧團能夠為社會提供優(yōu)質(zhì)的佛教文化產(chǎn)品那么這種“供養(yǎng)”就是佛教發(fā)展的經(jīng)濟基礎,,信徒滿足了自己的消費欲望,這種“供養(yǎng)”就是健康的,、良性的,、無害的。反之,,如果僧團不能夠為社會提供優(yōu)質(zhì)的佛教文化產(chǎn)品還要得到這些“供養(yǎng)”,,那這種“供養(yǎng)”就是病態(tài)的、惡性的,、有害的,。按照市場規(guī)律理解,高額的商品價格購買了低品質(zhì)的商品價值,,長期如此就會被消費者“淘汰和拋棄”,,導致商品供應方“退市”。巨贊法師大聲疾呼的“自養(yǎng)”就是意識到如果僧團不能夠提供優(yōu)質(zhì)佛教文化產(chǎn)品就不要參與社會交換,,最后的結果就是被社會拋棄,。
按照“生態(tài)動力”理解,建國初期的佛教界面臨了這個生態(tài)動力自驅動力不足甚至消失的困境,,在經(jīng)濟基礎上,,國民生產(chǎn)總值偏低,社會經(jīng)濟收入偏低,,人民群眾收入偏低,,整體國家經(jīng)濟水平偏低,經(jīng)濟能力的不足無法滿足“生態(tài)動力”的第一個自驅條件,;同時由于新中國的成立,,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移除,讓包括佛教徒在內(nèi)的廣大中國人民對未來充滿希望,,雖然物質(zhì)上還處于匱乏狀態(tài)但是心中充滿希望,,對社會充滿希望,對國家充滿希望,對自身充滿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大踏步地邁向新的征程,,充滿活力的社會讓“人生實苦”的理念失去了思考的空間。人民群眾充滿陽光的心理狀態(tài)和充滿活力的社會運轉機制讓佛教“生態(tài)動力”失去了自驅的動力來源,,如果佛教僧團在這個大的背景發(fā)生變化的情況下還不能“調(diào)試”,,那只能“坐以待斃”。
按照佛教傳統(tǒng)僧寶是“人天師”,,理想的“佛教法師”是無所不能的,,是佛陀精神傳承的在世弟子,而且僧寶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個體而是包括因地釋迦牟尼在內(nèi)的古往今來,、東南西北,、已生往生再生的所有僧侶的集合體,這是僧團的本質(zhì)含義,,當下活躍在人間社會的僧侶只是這個“神圣僧團”的一部分,。按照佛教傳統(tǒng)解釋僧侶是佛教徒尤其是居士群體的精神指導者、行動領導者,,既是精神生活的導師,,又是物質(zhì)生活的楷模。但是,,舊中國國情下大部分僧侶已經(jīng)失去了這種符合“人天師”標準的“佛教師范”,,這不僅是巨贊法師提出“新佛教”的現(xiàn)實基礎,也是太虛大師等高僧大德提出佛教革新運動的現(xiàn)實基礎,。在巨贊法師看來,,新中國需要新佛教,新佛教更需要“新僧侶”,,通過參與新中國建設,,通過參加思想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提升自己的社會覺悟,,就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新僧侶”。他提出,,“參加大雄麻袋廠工作的僧尼們的性質(zhì),,大約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對于佛教信仰相當堅定而保守,,但是缺少大乘佛教的實踐工夫,。常常根據(jù)主觀的愿望,期待著一個適合自己要求的環(huán)境,,得以提高自己的修養(yǎng),,而不能在人我是非之中檢討自己主觀的錯誤,,克服自己的煩惱,去適應環(huán)境,提高修養(yǎng),。因此對新社會的一切,有前進的心無前進的力,。第二類對于佛教信仰旣不深,,也沒有提高的要求,只是紡一天麻拿一天工資,,其他都無所謂,,有時不免因為重視個人的利益而忽略全體利益,影響生產(chǎn),。第三類是熱心佛教事業(yè)而缺乏事業(yè)經(jīng)驗,,看事太易,自信太強,,在實際工作中常常失敗,,致生煩惱。這都是長期在封建社會里養(yǎng)成的缺點,,而我們沒有用全副精神,,想辦法教育他們,改造他們,,不能不引咎自責,。”
巨贊法師從本質(zhì)上通過“佛教生產(chǎn)化”讓廣大僧侶改變傳統(tǒng)經(jīng)濟生活方式,,進而獲得“新僧侶”的覺悟,,才能保住“一領袈裟”,重新被新社會接受,。巨贊法師的“新佛教”就是在“生態(tài)動力”失能的情況下,,為佛教發(fā)展和僧團生存提供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這個邏輯就是巨贊法師提出“佛教生產(chǎn)化”的最大的經(jīng)濟邏輯,,辦廠自養(yǎng)就是通過自養(yǎng)提高修養(yǎng),,從而達到弘揚佛教的目的。這是巨贊法師“佛教生產(chǎn)化”的目標指向,,在實現(xiàn)這個循環(huán)的過程中“佛教學術化”是弘揚佛教的基本條件,,沒有文化和學識是不可能為社會提供優(yōu)質(zhì)佛教文化產(chǎn)品的。但是在自養(yǎng)問題上巨贊法師是因為建國初期的經(jīng)濟生活實際提出來的,,巨贊法師也不完全否定健康的,、良性的、無害的“供養(yǎng)”但前提是要為社會提供積極的服務,。巨贊法師的關于“新佛教”的兩個基本主張是通過解決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問題,,也就是僧團的生存問題,,再完成佛教的發(fā)展問題。從自養(yǎng),、修養(yǎng)到弘揚,,看到巨贊法師對“新佛教”設計的良苦用心,“新佛教”建設是新中國佛教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一劑良方,。
參考文獻:
1.巨贊:《大雄麻袋工廠試辦開工》,,載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三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1013頁,。
2.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從大雄麻袋廠的加工訂貨說起》,載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807頁。
3.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從大雄麻袋廠的加工訂貨說起》,,載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807頁,。
作者:彭宇,,男,漢族,,1979年2月出生,,山東聊城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科學導報·現(xiàn)代教育》
(責任編輯:土火)







 “護眼臺燈”亂象調(diào)查
“護眼臺燈”亂象調(diào)查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AI打標”背后有哪些隱患,?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AI打標”背后有哪些隱患,? 救命的醫(yī)療設備,,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
救命的醫(yī)療設備,,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 原價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不到百元
原價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不到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