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是唐代詩人王昌齡在《從軍行(青海長云暗雪山)》之中的名句。而"樓蘭"在唐詩中的"戲份",,僅在《全唐詩》中,,就高達二十五場。
作為漢代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樞紐,,樓蘭于當時的中原王朝而言,,最主要的價值還是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烧缤醪g筆下的樓蘭一樣,,后人在很多時候想起這個地方,,卻總是將它和戰(zhàn)爭聯(lián)系在一起。
人們產(chǎn)生這樣的聯(lián)系,,確實和樓蘭的實際情況有密切關(guān)系,。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樓蘭是"絕對"的西域,,與玉門關(guān),、陽關(guān)這樣的中原進入西域的"門戶"全然不同。所以出于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心理的差異,,樓蘭這個因為傅介子斬樓蘭王一事而走入中原人視線的西域國家,,就被當做了"不破樓蘭終不還"這些詩句中西域邊地戰(zhàn)爭的代名詞。
在把"樓蘭"當做一個代名詞的時候,,人們其實并沒有將樓蘭國這個國家太多地牽扯進其中,。就像如今網(wǎng)絡(luò)語言中說"我想吃檸檬",我們并非是此刻真的對檸檬這種水果有什么想法,,而只是想借此表達自己內(nèi)心的一些感受,。所以王昌齡等人提起"樓蘭",也只是把這里當做一片征戰(zhàn)的沙場,,由此來抒發(fā)自己的保家衛(wèi)國,、建功立業(yè)之志。
而除了成為西域邊地戰(zhàn)爭的代名詞,,"樓蘭"在很多人的眼里還有一個象征——中原對西域的統(tǒng)治,。前面我們提到,樓蘭這個西域小國走入中原人的視野,,與傅介子斬殺樓蘭王一事密不可分,。
盡管在此次出使期間,,龜茲和樓蘭的國王都對傅介子一行漢朝使者展現(xiàn)出了熱情,,也當著傅介子的面反思了自己與匈奴勾結(jié)的不當,,但傅介子還是察覺到這些人"躁動"的心,。所以出使結(jié)束后,傅介子盡管已經(jīng)利用從樓蘭和龜茲國王那得來的匈奴使者的下落線索斬殺了那些挑事的匈奴使者,,但還是向當時把持著朝政的大將軍霍光請命,,希望斬殺龜茲國王以儆效尤,。
在出使時,傅介子發(fā)現(xiàn)西域的國王比大漢的皇帝"親民"得多,,出行時和百姓們挨得很近,。所以傅介子覺得他完全可以借此機會刺殺心已經(jīng)明顯向著匈奴的龜茲國王,來震懾西域其他不安分的小國,。不過霍光覺得龜茲太遠,,再專門跑這一趟不太劃算,所以讓傅介子把刺殺對象改成樓蘭國王,。
不過傅介子也不急,,見樓蘭王不愿見自己并受賞,便帶著財物往樓蘭邊境走,。他還讓翻譯轉(zhuǎn)告樓蘭王,,如果不接受這些賞賜,那他就要把這些財寶送給其他國家的國王了,。
樓蘭王眼看著快到嘴的鴨子要飛了,,便終于按捺不住,邀請傅介子赴宴,,好讓這個漢使把財寶留下,。結(jié)果樓蘭王把自己都喝醉了,傅介子還是沒把賞賜給他,,還說漢朝天子有密令要給樓蘭王,,要他隨自己去帳中。
對付一個醉酒大漢多容易啊,。傅介子命手下兩名壯士抓住樓蘭王,,從背后一人給了樓蘭王一刀。樓蘭國的權(quán)貴們得知了王的死訊,,驚恐四散,。而傅介子卻沒再動這些人,只說樓蘭王這是不忠于漢天子,,他只是奉命來懲治罪人,。至于新的樓蘭王,漢天子已經(jīng)決定將由樓蘭在中原的質(zhì)子來當。
所以因為這層緣故,,因為樓蘭王是站在中原對立面的勢力,,人們便將"樓蘭"視作敵人的化身,一個被中原壓在腳下的敵人的化身,。這也是我們總覺得"樓蘭"二字自帶一種兩軍對峙之"殺氣"的原因,。
且當"樓蘭"有這層象征意義的時候,再以"樓蘭"入詩的作品便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歌頌?zāi)橙嗽趹?zhàn)場的豐功偉績,,比如"前年斬樓蘭,,去歲平月支";一類寫為國拋頭顱,、灑熱血的雄心壯志,,比如"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至于樓蘭最終消失在西域的綿綿黃沙之中,,并非是因為戰(zhàn)爭,而是因為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
兩漢至魏晉,,樓蘭國都一直處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發(fā)揮著其作為絲綢之路要塞的作用,。但河流改道帶來的干旱,,最終還是讓這座極有特色的西域小國成為"過去式"。
而往后,,便只剩"樓蘭"一詞還繼續(xù)活在詩文間,。
(編輯:月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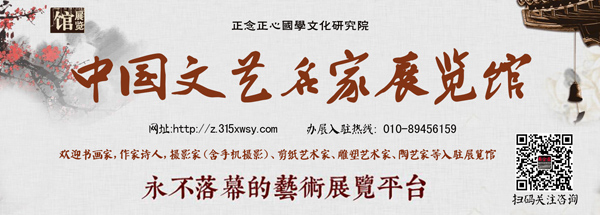







 “護眼臺燈”亂象調(diào)查
“護眼臺燈”亂象調(diào)查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AI打標”背后有哪些隱患?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AI打標”背后有哪些隱患? 救命的醫(yī)療設(shè)備,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
救命的醫(yī)療設(shè)備,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 原價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不到百元
原價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不到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