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攝

“童工”楊某朋65歲的老奶奶在茶樹叢間尋找和挖掘蟲草。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攝
近日,,有媒體曝光,,江蘇省常熟市一些服裝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開了社會的一道傷口,。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未滿16周歲,、本應(yīng)在課堂上讀書、無憂無慮地度過青春時光的孩子,,站到了機(jī)器旁進(jìn)行高強(qiáng)度的勞動?他們及其家庭是被欺騙還是主動作出的選擇?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鄉(xiāng)貴州省安順市進(jìn)行探訪。
年輕人“不讀書就打工”
安順市毗鄰貴州省省會貴陽市,,是我國最早確定的甲類旅游開放城市之一,。市內(nèi)有馳名中外的黃果樹、龍宮兩個國家首批5A級旅游區(qū),,擁有“中國瀑鄉(xiāng)”“屯堡文化之鄉(xiāng)”“蠟染之鄉(xiāng)”“西部之秀”等美譽(yù),。
安順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區(qū),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這片風(fēng)景如畫的土地上,。
當(dāng)?shù)厝私榻B說,,新中國成立后,,十二茅坡曾是軍馬場的分部之一,為部隊繁殖養(yǎng)育軍馬,。上世紀(jì)70年代軍馬場被撤,,十二茅坡的農(nóng)業(yè)開始興起,出現(xiàn)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藥材產(chǎn)業(yè)的公司,,還有從事禽業(yè)的公司,漫山遍野種植了茶樹和煙葉,。
這片地廣人稀的前軍馬場上,,“原住民”并不多。如同工地附近經(jīng)常出現(xiàn)打工族聚居區(qū)一樣,,隨著各種企業(yè)的興盛,十二茅坡也開始吸引那些偏遠(yuǎn)地區(qū)的人前來淘金,。
外鄉(xiāng)人在這里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購買下破敗不堪的房屋,,自此駐留。
楊某朋(本版圖文中人物均不顯示全名--記者注)是此次媒體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隨著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間破舊的房屋里。
記者費盡周折找到王某英時,,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樹叢間,,蜷伏著身體,扒開茶樹枝丫,,在茶樹的根部小心而費力地挖掘蟲草,。
“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能尋找蟲草?!彼玫纛^頂?shù)牟铇渲φf,,因為大量的采掘,蟲草已經(jīng)難以找尋,。
“這里的蟲草沒有西藏的那么值錢,。”她說,,為了找尋到收購價為每根1.5元的蟲草,,需要運氣,更需要勞作,,“彎著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滿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鎮(zhèn)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本寨鄉(xiāng)。寨子曾被火燒了3次,,“沒法住了”,。于是,2011年,,他們遷徙到十二茅坡,。
購置“新家”花費了3萬多元,幾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買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錢,,家里由此欠下了債務(wù),。
迫于經(jīng)濟(jì)壓力,老人的獨子楊某海--“童工”楊某朋的父親--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勞累的體力活,,下雨天還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給家里的錢也不多,,過年過節(jié)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來,。”王某英說,。
在“童工”楊某朋外出打工前,,65歲的王某英帶著他和他的兩個妹妹留守,艱難地一起生活,。
老人說,,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讀書,“長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實實在在地承受著經(jīng)濟(jì)上的壓力,楊某朋此前在鄰近的雞場中學(xué)念初一,,“喜歡玩手機(jī),,管不了,孩子自己也不想讀了”,。
今年春節(jié),,也就是15歲的楊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級第一學(xué)期后,一個“老板”來到他們家門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帶孩子出門去打工賺錢,。
根據(jù)老人和當(dāng)?shù)孛癖姷拿枋?,眼看著老家和“新家”周圍的年輕人都出遠(yuǎn)門去打工,長輩們似乎已經(jīng)確認(rèn)了“年輕人就該出去打工”的鐵律,,年輕人“不讀書就打工”儼然成為無需討論的固定模式,,沒有其他選擇。至于什么年齡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違法等問題,,他們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家長和孩子都有這樣的認(rèn)識,,就很容易和前來招工的“老板”達(dá)成共識。
當(dāng)時,,“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關(guān)心兩個問題,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沒有著落,,安全有沒有保障,,有沒有誰能管教孩子讓他不要學(xué)壞。對此,,“老板”說,有老板管著,,沒事的,。
大人關(guān)心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工資。雙方口頭約定,,過年時,,“老板”將孩子和錢一并送回來。
關(guān)于工資的數(shù)額,,低收入的鄉(xiāng)親們很容易滿足,,往往是“老板”報出一個價格,父母感覺“大體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這樣,,今年農(nóng)歷正月,在鄰居眼中“有點叛逆”的楊某朋被父母交給“老板”,,“老板”承諾保證孩子的安全,。隨后,楊某朋便和后來出現(xiàn)在新聞里的“童工”一道坐車去了廠里,。
王某英和他的兒子兒媳并不認(rèn)識前來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產(chǎn)生信任,是因為有一個當(dāng)?shù)氐某赡耆嗽凇袄习濉蹦抢锔蛇^兩年,,認(rèn)識對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壞事的”。
至于孩子到“老板”的工廠每天干什么活,、有沒有任務(wù),、工作的時間有沒有上限等問題,“什么都沒說,?!崩先藫u搖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孫子學(xué)習(xí)成績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讀書,,“不怎么服管教,讓他出去吃點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再看他愿不愿繼續(xù)讀書?!?
這是楊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說,家里不指望他掙多少錢,。
楊某朋到了工廠后,,曾給家里打過電話,但沒寄過錢,。他在電話中告訴老人,,“別擔(dān)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錯”,。
老人帶著他的兩個分別念三年級和四年級的妹妹,繼續(xù)在十二茅坡留守,。
楊某朋的離開,,并未顯著減輕一家人的生活壓力,老人仍然過得非常拮據(jù),,盼望著能在撫養(yǎng)兩個孫女長大的間隙,,能有點零工做。
但這個65歲的老奶奶在勞動力市場上并沒有什么競爭力,,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掙幾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來的規(guī)劃,,生活的艱辛迫使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視當(dāng)下怎樣能活得更好,。就這樣,少年楊某朋離開十二茅坡,,成為一名“童工”,。
“家里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發(fā)現(xiàn)的“童工”中,14歲的黎某龍和楊某朋一樣居住在十二茅坡,,兩人的房屋前后排挨著,。
黎某龍的家里擺放著一臺“songli”牌電視機(jī),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筆記本電腦差不多,,此外,,除了電飯煲、已不能脫水的老式洗衣機(jī),、電燈,,就沒有了任何電器。
房屋的墻壁裂開了口子,,石灰大片脫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磚。
對于記者的造訪,,黎某龍的母親楊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沒進(jìn)過學(xué)堂,連名字都不會寫,?!彼L(fēng)一般地跑出去,叫來自己的親戚,、同時也是鄰居的熊女士和記者一起交談,。
前些年,黎某龍48歲的父親黎某昌在安順等鄰近地區(qū)打工,,維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龍也開始打工后,,父親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掙得更多,。
黎某龍是家里的第二個孩子,,16歲的姐姐黎某健現(xiàn)在念初三,成績比較好,,獲得了獎狀,,希望能繼續(xù)念書;10歲的三妹正在念小學(xué)三年級;8歲的四妹念一年級。
熊女士告訴記者,,楊某妹一家生活的貧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來,這種極度的貧困,,是黎某龍小小年紀(jì)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幾天,,楊某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碰巧有人過來收廢品,,她就把一個廢舊的烤火爐子當(dāng)廢鐵賣了,,3毛一斤,賣了15元,?!毙芘空f,“她靠這15元支撐了幾天,,現(xiàn)在又沒有錢了,。”
“孩子上學(xué)的時候,,楊某妹會一個人吃午飯,,中午從來沒有見她吃過肉?!毙芘苦咧鴾I說,,楊某妹經(jīng)常用一點辣椒、加上沒油的野菜,,就著一碗飯,,沖點水,“泡著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卻沒錢了,發(fā)燒,、頭疼,,還暈倒了,我就借給她100元,,讓她到醫(yī)院去看看,。”熊女士說,,“沒想到,,過了幾天,她把錢還給了我,,說自己在床上睡了幾天,,多喝開水,沒去醫(yī)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這一家子住在安順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貓營鎮(zhèn)某村,,因為那里的房子已經(jīng)破舊得無法住人,,“實在沒辦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這個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機(jī)會的地方,楊某妹希望能分擔(dān)丈夫的壓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時候,,我就去?!弊屗趩实氖?,沒文化還得照顧孩子的婦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長時間干活的人,“我很難打上工,,一個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錯了,。那些老板說,‘你是帶娃娃的人’,?!?
46歲的楊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補(bǔ)貼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讓一家人吃上飯,,“實在沒錢了也能賣一點錢”。
盡管生活得非常節(jié)儉,,但這個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萬多元的外債,。
債務(wù)源于購房,也因為醫(yī)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兒黎某芊不小心摔傷了手臂,,在紫云縣醫(yī)院治療,花了1萬多元;前年,,四女兒黎某歡也曾到貴陽做過手術(shù),,花了5000多元。
這樣貧困的家庭,,為什么會生育4個孩子?楊某妹稱“大家都這樣”--在偏僻的山鄉(xiāng),一帶又一代的老人傳遞著“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觀念,,認(rèn)為多幾個孩子,,孩子們之間也相互有個幫襯。
夫婦倆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開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讀書,。
念幼兒園時,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們勉力維持,。到了義務(wù)教育階段,,仍需要給孩子一定的生活費,為了安全,,兩個女兒每半年還需要分別交納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費,。
這些開支讓這個家庭一直處于困境?!凹依飾l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睏钅趁谜f,,自己勸過孩子繼續(xù)讀書,可兒子說,,家境不好,,自己成績也不好,“不如出去掙點錢”,。
“我們就讓他出去試一試,,如果能適應(yīng),以后再說,?!睏钅趁谜f,“如果適應(yīng)不了,,就回家繼續(xù)讀書,,長大一些以后,再決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龍在念完小學(xué)六年級后,今年開始外出打工,。無論是在紫云縣的老家,,還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幾乎所有離校的年輕人都出門打工了,。在殘酷的生存壓力面前,,沒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屬于“童工”。
黎某龍沒有手機(jī),,每次和家里聯(lián)系都要借別人的電話,,如果家里打來電話,也需要打通別人的手機(jī)后,,約定一個時間再撥打過去,。
電話中,黎某龍告訴家人,“老板”對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時也會抱怨,說加夜班受不了”,。
聽見這樣的話,,楊某妹就覺得心里難受,勸孩子回來,,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堅持1年,“過年回來了再看”,。
黎某龍離開家庭的過程,,和楊某朋幾乎是一樣的。
“‘老板’到我家門口來,,說帶孩子出去打工,。”楊某妹回憶說,,對方提出工資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
至于具體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長時間,、必須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證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細(xì)節(jié),,雙方并沒有明確議定,。
雙方也沒有簽訂任何書面的合同,僅僅口頭約定,,過年時“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時候把錢一并交給大人。
為了讓“老板”對孩子好一點,,心疼孩子的楊某妹還給“老板”送了花生核桃,,這是她當(dāng)時唯一拿得出手的禮物。
楊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將自己孩子帶走的“老板”姓甚名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老板”還是“中介”,。
這些沒有太多社會經(jīng)驗的父母,堅信“老板”會恪守當(dāng)初面對面許下的承諾,。
在采訪中,,對于記者的提問,楊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記者只能不斷地從不同側(cè)面和她交談,盡力拼湊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內(nèi)心世界。對于“是否相信過‘知識改變命運’”“周圍有沒有人通過讀書考上大學(xué)而獲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復(fù)制那些‘榜樣’們的人生”等問題,,盡管記者用最平易的話進(jìn)行了“翻譯”,,楊某妹仍顯得茫然,沒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記者輾轉(zhuǎn)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韋某勝家里后,聽到的是同樣悲傷的故事,。
15歲的韋某勝居住在安順市寧谷鎮(zhèn)某村,,家門口就是學(xué)校,記者到訪時,,學(xué)校里正傳出瑯瑯讀書聲,。
韋某勝79歲訥口少言的爺爺韋某華呆坐在火爐旁,爐里燃燒著他砍來的樹枝,,老人的背部幾十年都長著一個碗大的瘤子,。火爐旁還有78歲病重的奶奶--她的身體狀況看上去非常差,,鄉(xiāng)鄰說,,她“不能動,不能講話,,坐著就不能起來”,。
韋某華共有5個兒女,目前隨小兒子韋某平--“童工”韋某勝的父親--一起生活,。
韋某華說,,小兒子從未念過書,“沒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廣東等地打工,“干體力活”,。今年,,因為母親病重,韋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護(hù)母親,,偶爾去打零工。
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透出這個家庭的貧困:石頭砌成的房子已經(jīng)裂口,,裂口最寬的地方,,足以將手掌放進(jìn)去,“要不是用棍棒撐著,,可能就會垮”,。
貧窮深深地改變了這個家庭,,“有時甚至連吃鹽都成問題”,幾年前,,韋某勝的母親決絕地離開了這個家庭,。
“雖然窮,我們還是盡量節(jié)約,,想讓小孩多識幾個字,。”韋某華盯著記者的眼睛說,。
在鄉(xiāng)鄰們看來,,小學(xué)和初中階段盡管交錢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種名目的費用,,“還是得花錢”,。而外出打工,雖然未必能賺多少錢,,“但過年起碼能買一件衣服”,。
部分鄉(xiāng)親已經(jīng)聽說了韋某勝成為新聞中的“童工”的事,但他們并不認(rèn)為做“童工”是錯誤的決定,,相反,,是一個“不得不這么做”的決定,“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要養(yǎng)活這一大家人,他父親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歲的爺爺還得去干農(nóng)活,。”鄉(xiāng)親們說,,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幾分,老人種的所有糧食“值不了幾個錢”,,“現(xiàn)在種地基本不賺錢,,年輕人還能喂牛喂馬,可是他一個快80歲的老人已經(jīng)不能喂牛喂馬了”,。
按照這樣的邏輯,,鄉(xiāng)親們認(rèn)為,在韋某勝的父親因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況下,,韋某勝成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鄉(xiāng)親們掰著手指頭介紹說,村里14~18歲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計有一二十人,。他們并不清楚“童工”的定義,,對于其中16歲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數(shù)量并沒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韋某勝一個人”,。
在交談中,鄉(xiāng)親們固然并不認(rèn)為“讀書無用”,,但對“讀書有用”的觀點也并不堅守。對于是否每個家庭都能承擔(dān)高中,、大學(xué)階段的投入,,以及“砸鍋賣鐵”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帶來體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們并不抱有絕對的信心,,“有一些大學(xué)生也掙不到錢”,。因此,對于那些成績較差,、未體現(xiàn)出讀書潛質(zhì)的孩子,,這些農(nóng)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棄,。
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一個令人擔(dān)憂的狀況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認(rèn)識前來招工的“老板”,,也未對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進(jìn)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實,。
當(dāng)?shù)赜袀餮哉f,曾有“童工”誤入傳銷行業(yè),。這樣的悲劇,,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探訪中,,貧困是顯而易見的,,對很多問題的答案,卻藏在每個人的心里,,沒有人說出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貧窮,、對教育投入和產(chǎn)出的不同理解,,讓孩子們離開了課桌,過早地在成人世界的驚濤駭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結(jié)實的風(fēng)帆,。(編輯: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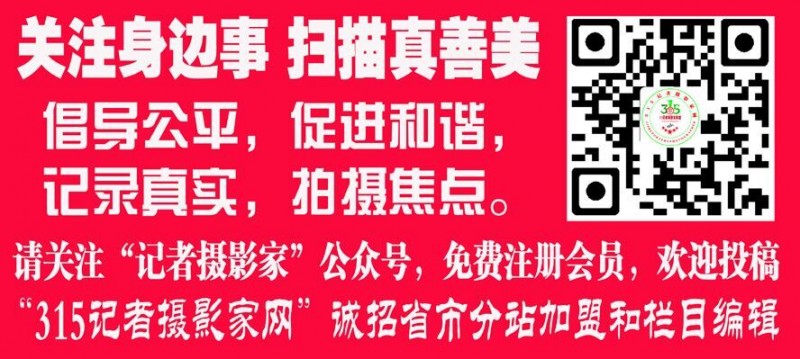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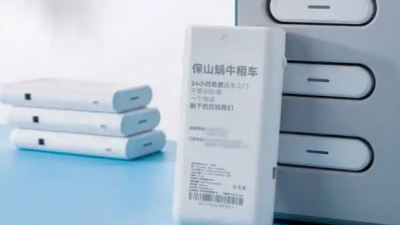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AI打標(biāo)”背后有哪些隱患,?
AI賬號成起號新套路 多手段繞過“AI打標(biāo)”背后有哪些隱患,? 救命的醫(yī)療設(shè)備,,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jī),?
救命的醫(yī)療設(shè)備,,如何淪為個人提款機(jī),? 原價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不到百元
原價上千元“貴婦霜”網(wǎng)店賣不到百元 誰在販賣我們的個人信息,?
誰在販賣我們的個人信息,?